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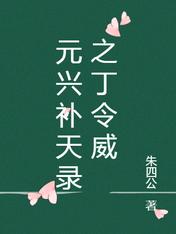
其他类型连载
东晋元兴年间,江州庐山,一僧一道,一场遮遮掩掩的宏大法事,一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终极救赎,不曾料到,引来了一个远方来客,非生,非死,非人,非众生。
主角:法空,丁令威 更新:2022-12-11 02:37:00
扫描二维码手机上阅读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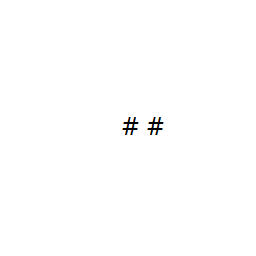
男女主角分别是法空,丁令威的其他类型小说《元兴补天录之丁令威》,由网络作家“朱四公”所著,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,本站纯净无弹窗,精彩内容欢迎阅读!小说详情介绍:东晋元兴年间,江州庐山,一僧一道,一场遮遮掩掩的宏大法事,一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终极救赎,不曾料到,引来了一个远方来客,非生,非死,非人,非众生。
民国三十六年,按西元纪年,唤作一九四七年。这一年夏天,农历六月,江南八府一州,如同往年一般,热浪灼人。
天地之间,尽是一团炙热,透不进一丝风。身处室外,烈日暴晒,躲入屋内,酷热难当。暑气之中,本就心烦气躁,乏力懒动,偏偏此时正值双抢,正是一年之中,江南农户最为忙碌的节令。
月初,在秧田里打下第二季稻种,打完二季稻种,又一刻不闲,去收割一季稻。热风吹过,稻子见风而熟,谷熟粒落,得赶在两三天内收割到户,半分耽搁不得。当此之时,勤俭到家的江南农户,也往往不得不雇几个江北来的稻客,抢收抢打,颗粒归仓。
割稻是个苦差事,活重赶急,天气也不照顾。只道是硬扛住暴晒,谁料,老天爷又会突然翻脸,忽地就飘来一团乌云,不由分说,劈头盖脸,就是一阵瓢泼大雨,哗哗啦啦,漫天而下,把田中人淋得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。
大雨浇过,复出烈日,水汽蒸腾,把田间闷得如同蒸笼一般,这比单纯的暴晒更令人备感炙热。每到此时,总有些年轻人按捺不住心火,握紧手中的镰刀,从滚滚稻浪丛中,昂起头颅,望天而吁,但更多的人,却只是埋下头去,只说熬过去罢。
割完这一季稻,紧接着平整水田,插二季稻的秧。低头遍观水中天,退步原来是向前,腰一路弓着,一天秧插下来,硬得都直不起来。但插秧毕竟没有割稻那么赶,农户们都是咬咬牙,靠着自家那点人手做完,不舍得再外雇帮手了。
这一季固然辛劳,他季也未尝能得以稍歇,采桑养蚕,放苗起塘,世间种种活计,莫不艰辛如是,如此一年忙碌,才撑得起一户衣食自足。在这片土地上,日升月落,寒来暑往,华夏先民,生死交替,歌于斯,哭于斯,聚一族于斯,这般生活,已有数十百辈之久。
且说在江南腹地,太湖南岸,湖州吾犹县虎坼镇,有一偏僻小村,名唤夏柏村,合计老幼丁壮,也不过四五百口。旧时江南,小小村落,大多是同族人聚族而居,一族人共立一族祠。这夏柏村,地处一隅,杂姓少到,合村老小,别无他姓,都是姓了个张,共立了个族祠。
夏柏村得名,来自村庄水口处的古柏树。七株古柏,错落成林,进村大道,正从这片古柏林中穿过。大树参天,不知年岁,胸径已有三四人合抱,仍是生机盎然,枝繁叶茂。故老传说,这几棵古柏是夏禹亲手所植,故称夏柏。
曾有一个过路的风水佬,自称姓赖,清隽精瘦,一身黄布袍,背负一个黄布包,一走到这夏柏村口,突得停下脚步,当即取出罗盘,就地摆下,又一番游走,掐指推算片刻,直呼结棍赛雷了不得。
有几个村中老叟,当时正在古柏下纳凉,见这番作怪,心生好奇,连忙拉住他,请他说道说道。这赖氏立在当地,环顾众人一番,聚足了气势,才喟然叹道:好格局!好格局!真真不知是哪位前辈的手笔!
据这位赖大师所说:原来村口这七棵古柏,恰成一个北斗形状,北斗位置,世世多有变易,而这些古柏的位置,暗合了史上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的北斗星相。更神奇的是,这夏柏村族祠所在,正是这个北斗勺柄所指向的北极星位。
不知是贵宗的哪一代先祖,延请了绝世高手,巧借星斗之力,立族祠于此北极星位。这一族之内,所出大富大贵之人,将会如同这七棵古柏的树叶,代代相继,难知其数。
那几个老叟听到这番说法,彼此对看一眼,先是面面相觑,突然就一阵哈哈大笑。赖氏见这些村民难知难信,也只一笑,不再多言,收拾好零什,长袂飘飘,走了。这赖姓风水佬走后,村中人偶有说起,都只当个笑话来听,根本不放在心上。
世间的风水佬,就算再巧舌如簧,神乎其技,对生人生地,也不过只能骗上个十年八年,而村民们世代祖居于此,对树上的每一个枝桠,熟知得如同村中的每一个门阙,自然不会上这种当。这整个夏柏村,哪有什么大富大贵之人!
举目四望,合村都是庄户人家,以鱼米为食,桑蚕为生,日子都过得捉襟见肘。大富大贵?别说在本支族之内,从来未曾出过这般人物,从乡老耳口相传来看,就连这几株夏柏之下,也未曾有什么像样的大人物打马路过。
且不说杭城里的那些达官贵人,才子名士,就单看这当地父母官,在一地生民眼里,他们自然也是大人物,立县几百年来,本县实任县令,任期短短长长,尽数算上,已有数百人。往上细细数去,这些父母官们来来去去,都未曾有一人造访过这夏柏村。
在这个偏僻村落里,绝大多数族人,从生到死,辗转于此,这方圆十几里地,耗散了多少人一生的心力。他们所有的生老病死、悲喜苦痛,无人关心,无人在意,似乎连天地都漠然不知。虽说如此,但在夏柏村人看来,自己合而为一族,却并非毫无可夸耀处。
有些黄毛小子,每见村落鄙陋,生起妄自菲薄之心,老辈族人见了,不禁暗暗蹙眉,蹙眉之下,自然是有一番触及灵魂的说教。
后生仔,往远里看,有家谱为证,明明白白,我们可都是西汉留侯张良的后人,宗祠门前,更是高悬着“清河衍派,百忍传芳”八个斗大的正楷颜字,端庄静穆,令人肃然起敬,一望即知,这绝非寻常门户。
从近里说,距离虎坼镇不远的南浔镇上,就世居着另一支张家,人称“张家的才子”。南浔张家,和夏柏村的这个张家,往上细数,却都同出自一位老祖。这位老祖搬到湖州后,子孙开枝散叶,这才有了南浔、夏柏这两支。
当时的湖州,富豪家族众多,在巨富大族中,有一个公认的排称,所谓“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”,南浔张家,正是这头号的“四象”,在江南八府一州里,都是数得上的响当当人家。进入民国,这南浔张家的家势,更是烈火烹油、鲜花着锦,声惊海内,名动亚东,无需赘言。
而这大名鼎鼎的南浔张家,细说起来,却与夏柏村这个张氏本出同宗。这般说来,我们夏柏这一支张姓,自然也是小视不得。
这么一番教训,往往说得年轻人无言以对,讷讷而退,心里直道:这老爷叔真聒噪,一味卖老,下次可要离得远点。
这吾犹县夏柏村,有一户小夫妻,户主名叫张听讼。张听讼父母早亡,也没什么叔伯族亲在世,只有一个亲弟弟,名叫张无讼。这张无讼也不是读书的料子,早早的废了学业,又不安于农事,年纪轻轻,跑到杭城,帮一个东家跑生丝买卖,把家里一摊农活都丢给了兄嫂。
张听讼夫妇识字不多,张家也家小业微,虽然终日勤勉于农事,也只是勉强吃得饱饭,连富足都称不上。夫妇俩膝下只有一个儿子,名叫张铭华,这一年方才六七岁。这孩子初生时,江南已经沦陷多年,正是抗战中最艰难的时候。
也正是在那一年,远在西南边陲的昆明,住着一位大教授,人称宾四先生。他抛下杂务,专心写成了一本中国通史,只说是日寇势大,华夏只怕是守不住了。亡国在即,书生报国,只有满腔热血,一支秃笔。他拼尽全力去写就这书,原是心中仍有一个盼想:
假使我中华竟而真的亡于了贼寇之手,华夏子孙都已然沦为亡国奴,只要煌煌国史尚在,薪尽火传,代代子孙,只要熟知国史本末,不为贼寇秽史所惑。但得这一点火种未灭,我华夏文明就未曾断绝,他日复国,犹然有望。
而在太湖之畔的夏柏村,大字不识几个的升斗小民张听讼,也是这一年,得了这个宝贝儿子,同样眼见胜利无望,就给初生的儿子取名“铭华”。这名字却无太多深意,只是取了个字面意思“永铭华夏”而已。
话说到了这一年,过了夏至,正在读初等小学的张铭华就放了夏假。这个年纪的孩子,正是闯祸的行家,惹事的好手,帮忙乏术,添乱有道。不但田地里的活帮不上忙,就连稍大点的家务也不能放心交给他。
张听讼夫妇终日在田地里忙着农活,实在是照看不过来,只能由着他终日在家舍周围晃荡。而家舍周边,遍地塘泊,沟岔密布,水草杂生,万一稍有闪失,小夫妻俩可要后悔莫及了。两人几番商量,只得考虑把孩子送到外婆家去消夏。张家外婆,家却在建德县。
建德县在湖州以西三百里地,虽然距离不远,但地貌已有不同。湖州地处平原,自太阳升起,就晒得无遮无挡,自然酷热难当。而建德县却属于丘陵地区,四境有山,有荫有蔽,清风时来,夏日也就相对好过很多。
这两地农事,更有一番不同。湖州一年两熟,而建德县一年只种得一季稻,额外还得靠一点山货贴补家用。虽然全年收成略薄,但田务也相对清简,更兼之外家诸舅父正是当力之年,家中劳力充沛,因此远不似张家这般忙碌。
外家二老,都年过耳顺,颐养在堂,早已是不用下地干活,只需在家安排好一日三餐,再帮忙照看诸位舅父们家的一大帮孩子。多来一个张家外孙,倒也不算太多添担,而再得一个孙儿辈嬉戏膝前,更多得一份老来欢乐。
虽然不及湖州那般星罗棋布,满地尽是塘泊,但建德境内也颇多河道,其中较大的是新安江和兰江。两江在建德县内汇流,称富春江。富春江再往下,在富春县与浣江汇流,才叫做钱塘江。这钱塘江,因河道蜿蜒曲折,古称浙江,浙省就因此江而得名。
而从张家外婆门前流过的,正是这浙江的上游段,人称新安江。
新安江水量颇丰,又全由山溪汇聚成河,绝少泥沙,河水清澈见底,游鱼细石,直视无碍,两岸高山,寒树成林,群峰轩邈,负势竞上。蹲在船尾,扇红炭火,取一瓢江水,煮在炉上,听着茶声鼎沸,陪着满目山水,沿新安江泛舟而下,历来都是江南士大夫的一大乐事。
张铭华哪里长出过这样的雅骨,面对这一条江水,他充满了畏惧。父母送他来外祖家前后,已是再三警告:不得凫水。外祖又对他再三恐吓,掰着指头,细述反面案例,不外乎某年某月,某某家孩子私自下水游泳,被水鬼拖走,生不见人,死不见尸等等。
这一类事例鲜明、故事生动的小故事,在当地育儿经中,本就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与他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也无不在这种恐吓里长大。但要达成好效果,仅有口头恐吓,效果还是不够的,还要有“毋谓言之不预也”。
每当日暮,孩子游玩回家,父母只要看到湿了布鞋,就是扑将上前,一把揪住,一顿好打,两次三番,教训才真正生成。孩子们胆气虽壮,常惹事端,但还不敢藐视父母之命,因此,终日里只是聚成一群,沿着江畔游玩,躲躲猫猫,抓捉迷藏,尚未敢不顾警告,悍然下水。
这一日上午,又是个大太阳天。张铭华与那群伙伴在江边捉迷藏。这一局,轮到他去寻找藏人了。按规则,只见张铭华把头蒙在一垛稻草堆里,口中高声报数。不比他是个外来生客,其他稚童本就生养在当地,熟门熟路,十下数数未毕,早就四散藏好。
数十已毕,脑袋上还顶着几根草梗,张铭华从稻草垛里探出头来,正准备逐一搜找。恰在这时,抬头只见远处北边天空,有一个火球自西往东,疾速飞过。
此时,艳阳当空高照,晃得人都有些眼花,而火球依旧清晰耀目,足见其亮度之大,但这火球飞在极高极远,在地面看来,不过一婴儿拳头大小,又未发出任何声响,不是偶然抬头看见,一般人根本留意不到。
张铭华见得这个稀奇,连忙高声惊呼:“大家快出来看!快出来看啊!天上那是什么!”话音未落,只见那小火球去速极快,已是飞过东边山麓脊线,灭失在了天际。
小伙伴们听得这般呼喊,只当有奇事可看,纷纷从藏身处出来,却是什么也没看着。孩童们自也不蠢,只当是张铭华使的伎俩,骗他们现身。大家受骗之余,嬉闹一通,争说张铭华这个平地客,果然不够实诚,找不到藏人,就使计出诈。
下一局,就轮到张铭华去躲藏。为刚才被人笑话的事情,这孩子心里有点负气,“非得让你们找不着我”。他沿江上溯走得稍远,只见江边有一条巨石,一人多高,鼓囊囊的,又长又圆。这块石头其实一直都在这里,只是平日里绝大多个都没在水里,因此并不显眼。
最近江南连续无雨,上游给水不及,到了建德境内,沿江水一线,两岸群山已经露出老大一截坡脚,黄扑扑的。水面下降颇多,特显出这个石头尤为巨大。只见它的一头,已是深扎在水里,另一头却还长埋在江岸山坡的土石里,真是好长一块巨石!
张铭华又是搬来石块垫脚,又是伸手攀缘,小心翼翼,费了一番力气,爬上巨石石面。他站在石面上,弓着腰,曲着腿,四下张望,不免心生寒意。壮了壮胆,打算还是按原先想法,从另一面滑下去,躲到石后去。这可真是个好去处,小伙伴们找起来非得费点力气不可。
不料,这小孩沿着巨石,从那一面慢慢滑下时,却一下子没能收住脚。原来这巨石那一面的石下,竟有个见方两三尺有余的地坑,平时只淹在江水之中,也不知道是什么水物用来藏身的。张铭华整个人从石面滑下,一下子直接掉到坑里去。
这坑比小孩个头还高些,但张铭华要爬出去并不困难。他不见慌忙,手足并用,双手已经攀到坑外,这时脚上一蹬,人应该就爬出坑去了。不料脚上一使劲,却蹬落了一大皮湿土,哗啦啦滑落到了坑底。脚底失了力,小孩子手一松,整个人又掉回坑中。
张铭华挠挠头,在坑壁四下的看,找可以踩脚的地方。这才发现,刚被蹬下的那皮土下,露出个竖立着的石板面,颜色黝黑而冷峻。这小孩子尝试着用手拍拍石板,却是空鼓的声音,显见板后是空的。这下子勾出了他的好奇心:莫非这里面,竟是窖藏了什么宝物。
小孩的这个心思,却并非向壁虚造,而是其来有自。当地乡间,原就多有“挖窖得宝”的传说。
每逢历代承平之时,当地富商大贾迭出,几代勤俭传家,就积得好大家业。一到乱世,这些巨富之家举家外逃,一求轻便,二求安全,贵重之物不便携带,只得将其窖藏在地下,留待日后返乡时挖取。
但命运难料,造化弄人,这些窖宝人一旦离乡,不用说在有生之年能取回窖宝,就连数代之后,后世子孙能如愿返乡启窖的,往往都百户中而无一二。
陵谷沧桑,当年窖宝之地,日后有的仍旧为屋舍,有的却已改做田地。后来人有时整修旧屋,有时下田地里干活,就会挖到前人的窖藏,遂得暴富,这就是“挖窖得宝”。但是,往往在数年之内,这些意外得宝之家,也会莫名其妙的生出或大或小的灾殃。
对这类灾殃,有好事者解释说,窖宝之时,窖宝人必施行了诅咒之术。也有种解释说,窖宝人死后,惦记着自己的藏宝,一点魂灵不肯散去,千里返归,附着其上。后人挖窖得宝,非其有而取之,必然让藏宝之人怨恨,魂灵生事,从而给挖宝人造就了祸事。
西谚有云:“逐利如同山岳一般古老”,无论垂髫还是苍颜,对财富抱有梦想,这原本就是天性,财富当前,哪里管得了什么灾殃。张铭华从小耳濡目染,听到很多这样的传闻,所以对窖宝也大有巴望。见这个中空的石立板,只说板后必是挖了个侧洞,正是一个窖宝。
只见他伸出手来,抠抠索索,往石板边缘摸,想从边上着力把石板掀开来。不料这块石板比想象的要大,几乎有两三尺见方,摸到边沿之后,继续往内摸,却还能摸到侧壁。这般推想起来,难道不是一个以石板封着的窖洞,倒像是个方形的大石匣子。
正想着这是什么鬼,莫非是个石盒子?就只听得石盒子里传来一声清晰的“哈哈”大笑声,接着石板背后似乎被谁轻轻一推,板面上的残土,嗦嗦的落到坑底,而眼前这块石板,却已经缓缓的向着张铭华打开了来。
这一下,可把张铭华唬得魂飞魄散。
与其他乡间一样,当地鬼故事也特别繁茂,几自成一套鬼话系统。在这些鬼故事里,有一种恶鬼,名叫泰相,身材高大,总有两三层楼高,而又身无三两肉,瘦如麻杆,简直像一个行走的撑衣杆。据说这泰相,凶狠异常,战力可怖,灵界之中,除了门神,谁都挡他不住。
但这么一个鬼中干才,鬼生却素乏追求,平日里别无他好,只是专爱吃小孩,而且不折不挠,孜孜以求,吃得费尽心思,不择手段。
且不说那些无父无母,夜里流落荒野的可怜孩子,即便小孩子们有家可归,有门神护持,泰相也能仗着身高臂长的优势,趁他们熟睡之际,从窗户里伸进手来,把小孩抓走了吃。因为有这个民俗背景,所以当地有小孩的人家,临睡前必得嘱咐关窗封栓。
而传说里的泰相,每次出场,就是刚才这种标志性的“哈哈哈”一阵狂笑。
形势突变,期待落空,小孩吓得顾不得什么窖宝了,拼命想往坑外爬,但腿脚酥软,站都站不住,只得瘫坐在坑底,徒劳的蹬着腿,眼睛直勾勾的看着。亏得他在慌乱之中,还能看得清楚:原来这个石板一侧有轴,正是一个石函的门,而这个石门,正从内部被一点点的推开。
等到推开一大半的时候,就迎面看到石函门内,尽是满扑扑的白丝,宛如蛛网,七错八综,密布在石函面上,而石函内,似乎还有活物在动。张铭华满怀恐惧,瞪圆了眼睛,依稀只见一个瘦高个盘腿趺坐在石函里,正缓缓的伸出手来,轻轻拂开面前的丝网。
片刻之间,张铭华还惊魂未定,这石函门已然全开。函内面上那一层白丝,遇了从洞口透进来的熹光,如同冰山见日,很快就消融得干干净净,不见踪迹。没了遮挡,这才看清函内这鬼,头发不过尺许长,而全身衣裳已是破烂不堪,成了一片一片的褴褛,挂在身上。
乍一眼,觉得这个鬼个子挺高,但因为趺坐着,也尚不清楚有多高。更邪性的是,这个鬼奇瘦见骨,双颧高耸,脸上的皮松弛着,垂挂了下来,叠放在腿上的双手,几乎成了一副附皮的手骨,只是那指节颇显粗大,显见生前是个干得苦力的。
最令人称奇的却是那一双眼睛,正炯炯有神,略带笑意的看着小孩。在昏暗里,眸子里竟也能隐隐透出和煦的光。
张铭华见他眉眼之间居然带着笑意,想起传说里的泰相也是又高又瘦,以笑知名,内心加倍恐惧,战战兢兢的叫道:“鬼!鬼!鬼!”这喊“鬼”的吐字,虽然凄厉尖锐,其实并不响亮,原是变故之下,惊惧挤住了喉咙。
这鬼物听到这番尖叫,又“哈哈“的笑了两声。张铭华心道:“完了!完了!是泰相了!”不料他却接着说道:“小稚童,别怕,我,和你一样,是人。”也许是很久没和人说话,这句话说的有点磕磕巴巴,但口音倒也没差得太远,意思也还听得明白。
张铭华心里稍稍有点安定,在传说里,泰相这种鬼是不会说人话的。于是追问了一句:“那你是谁?”不料那人竟笑了起来,说:“我和你,到外面,去,晒晒太阳,再和,你说。”对张铭华来说,去外面正是求之不得,而且也更是放下心来,世上应该没有爱晒太阳的鬼。
见这孩童露出了许可之意,那怪人就伸出一只大手,瘦如鸡爪,一把抓住张铭华的后背。别看这怪人骨瘦如柴,力气竟也不小,手提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孩,也毫不费力。只见他单手半托半举,从坑里一跃而上,身形一出了地坑,也不在地面上垫个脚,而是拎着这孩子,直接腾空而上。
等张铭华反应过来时,已是身在云端,四周都是细粒的水汽,白蒙蒙的一片,虽在近处,也不能视物,登时又是吓得张口结舌。过了片刻,他才终于喊得出声,此时,那人已经拎着他,飞出了几十里远,两人的身下,正是近处的一座海内名山。
不比宋前,到了明清两代,经过诸多驴友的倾情推荐,这座奇山已是声名大噪,更有好事者,推扬其傲视群山,力压五岳。虽然到了此时,山道依旧险峻,登临颇有风险,行人尚不多见,但已是名声在外,尤其以“四绝”最为人所赞羡。
但这小孩平生也不曾见识过林壑之美,哪里识得什么名山,等他发现自己身在半空,吓得只想哇哇哭叫。好在两人去速极快,他还未“哇”得哭出声,那人已是轻轻一收脚,两人稳稳的落在了这座名山的山巅之上。
江南地貌,大体是平原,但点缀其中的,除了村舍、河流、湖泊和平林,也有诸多丘陵踞卧其间,但高山却是不多,方圆百千里内,就数此山最高。当日天气晴好,极目千里,只见众山俯首,延延绵绵,苍翠茫茫。
双脚落在实地,小孩这才回过神来,原来那人拎着自己,落在一块山巅巨石的顶上。这石顶一丈见方,颇为平坦。那怪人轻轻一撒手,将小孩放在巨石之上,自己却纵身一跳,飞身跃到了巨石之上一株老松树的枝顶,就在这松枝顶上,盘腿趺坐,四下瞻望。
这山本是一座石山,高山之顶,哪得土壤,因此它树难活,只在石罅缝中长得出松树。这些松树,餐风饮露,一个个修得仙风道骨,造型颇得几分韵味,只是生长极为缓慢,百十年老松,亦不过小孩手臂粗细。
这山松另有一样,也与寻常松树不同。大概是因为山风剧烈,松树往往也长不大高,即使是数千年的古松,树高也只不过一人半而已,而枝叶却如同顶盖,从四面旁逸斜出,形如大伞。虽然造型颇为瞻胜,但毕竟只是些松枝,树顶之上,也根本承不得重物,更何况是个人。
此时已经上午九点多钟了,日正东悬,山风劲吹,山松也随风来回摆动。那怪人坐在松顶之上,整个瘦如骷髅的躯体,也很自在的随风摆动。看他全身轻松,竟是坐得相当牢靠,这么大的风,也不曾把他从树上吹落下来,却把站在树下的张铭华看得目瞪口呆。
那人极目远眺一番后,颇有些惆怅,说道:“六百年来,此地黄白气盛,天下无两,时到今日,终于有些歇歇了。”一低头,见小孩站在石头上,瞪着双眼,呆呆看着自己,有点像是打破尴尬似的,对张铭华笑了笑,又问他姓名和年纪,张铭华一一作答。
听完小孩的答话,那人竟打了个哈欠,嘴里嘟哝了一句:“还真是有点饿了。”
艳阳在空,美景在旁,张铭华的心情原本已经有点放松,又见他问自己姓名年龄,和和气气,也已明白这绝非是个鬼物,只是个怪人而已,心里也已不再那么慌张。但突然听到这话,可把他吓坏了。
这高山顶上,除了自己,哪有什么可吃的?家里长辈有了什么吃食,往往也是:“这是桃酥,来,吃一个。”食前问名,自古以来,都是对食物表达尊重的一种方式。这个怪人刚才问自己姓名年龄,原来用意正在于此!这般看来,此人虽怪,倒是颇讲几分用餐礼仪。
张铭华战战兢兢,坐在那里,只待一死,半响未听得声响,抬眼望向那人,只见他说罢这句话,却也不曾点起蜡烛、铺上桌布、拿出刀叉,在脖子上围上餐巾,挤出芥末,只是依旧在松顶之上盘腿趺坐,不再出言,继续晒起了太阳,可能是晒得太舒服了,竟还微微阖上了眼。
正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,张铭华突然感到一丝丝冰凉的东西滑入嘴角,舌头略略感到一丝又一丝的凉意,这丝凉意甫一感受到,瞬间就消失在舌根之下。最初,他还以为是缕缕山风吹入口中,但这般连绵不绝,丝丝入口,入口之初,又隐约有点韧劲,显然不是山风。
正在纳闷,只听得四周传来一片悉悉索索的声音,张铭华抬眼四下一看,只见各式各样的山兽,正四面八方显身,往自己所在的巨石这边奔。
跑在最前面的,是一群短尾猴,正是本地特有种群。它们攀岩走树,又蹿又跳,正往这边疾速奔来。只见为首的那几只,已经是白须白眉,一身猴毛也已发白通透,根根如银,显见是不知多大岁数的老猴了。
往地上看,山兽们有成群的,也有跑单的,也正往这边齐聚而来。定睛看去,不但有狐狼狸鹿这般山间寻常动物,甚至在岩旁石罅间,还能看见蛇、蛙、老鼠、刺猬等昼伏夜出的动物,青天白日,堂而皇之现身,即使彼此是天敌,此时也顾不得争斗,只一心往这块巨石聚来。
张铭华全身顿时一阵鸡皮疙瘩,又惊又惧。想跑,又不知道怎么下得了这块巨石,但看四方八方都是山兽,又该往哪里跑。他想呼喊,警示那怪人危险已近,两人快快避开为妙,可是一时之间,已是吓得张口结舌,喊也喊不出来。
奇怪的是,跑到了距离巨石两三丈远的地方,这些山兽都停住了脚步。在陡峭的山间高高低低,错落不一,围成了一个密密麻麻,但又显见规则的圆圈,就连飞来的几只白鹤、金雕等鸟雀也从空中落下,悄然站定。众兽杂处,寂寂无声,就这么静静的站着,把巨石团团围定。
正不知这些山兽是发了什么颠,只见一只斑斓大虎,突然从半山密林里钻出。张铭华在山顶远远望见,不由唬得全身寒毛竖立,两条大腿软到发抖,吓得他一屁股坐在石面上,却见那老虎也不发一声响,只往山顶巨石奔来。
众兽见它来到,纷纷让出一条道。这老虎大摇大摆,也不顾其他,只一路奔到那根看不见的圈线位置,却也安安静静的站定,一双虎目,收敛住了凶光,倒见得满腔渴望,只往巨石之上那株古松上看。
顺着这老虎的目光,张铭华回转身,去看那人。只见他依然瞑目趺坐,对身边的动静似乎一无所知。但这小孩很惊讶的发现,原先看起来瘦如骷髅的一个人,现在竟然整整胖了一大圈,手上与脸上都有点肉乎乎的了,身体四周,还弥漫着一团若有若无的湿气。
这时,只见靠得最近的,在圈线上站着的那群山兽,开始低头做舔舐状,似乎在吃着什么极美味的东西。那几只白猴,一边用爪子往嘴里送,目光还热热的往上看,像在等着巨石上有人抛食一样。不一会,从圈线往外,低头舔食的动物也越来越多。
这一幕,让张铭华大感好奇,正看得傻眼的时候,不知道什么时候,那人已经从松顶上一跃而下,站在了自己身边。张铭华转身打眼一看,与刚才那瘦骨嶙峋的模样,已经判若两人,对,确实是胖若两人。
虽然称不上大腹便便,但也已经当得起一句“胖子”了。面部除了变胖,显得肉嘟嘟的,脸色还颇显滋润,泛着酒足饭饱后的幸福光芒。要不是那眉眼没多大变化,还是笑意俨然,张铭华几乎要怀疑这是换了个人了。
突然,张铭华又想到了什么,吓得退后两步,指着那人说:“你是千年僵尸!”张铭华自小就听乡里传说:这僵尸出来活动时,眼见都是胖的。但一旦静匿时,被人发现于藏身之处,却都是骨瘦如柴的模样,所谓“动胖静瘦”。
在传说里,有些修行有年,所谓千年僵尸,也能屈手屈腿的活动,甚至说些简单的话,但这种僵尸也非同寻常的厉害,一般的道门功夫根本对付不了。有时候,有些请来抓鬼的法师,功力有限,甫一交手,逃跑不及,被其逮住,当作宵夜,一顿吃不完,还会打包带走。
那人又是一阵哈哈大笑,回答说:“不是,我确实是人。小孩子,你想想,哪有僵尸白天活动的?”
虽然相处时间不长,张铭华见这人说话和气,做事又爽直,通透到了孩子般的天真,一看就是个好玩伴,内心其实是有点亲近这个人了,也不希望他真的就是僵尸,听到这人给出了一个强有力的理由,有点高兴的应道:“倒也是啊。”
那人见张铭华已经打消了顾虑,就对他说:“要不我们换个地方去玩,把这里让给它们?“说着,他指了指外面围了一圈的山兽。张铭华虽然不知“让给他们”是什么意思,但也顺从的点点头。那人又是一手抓着张铭华后背,腾空而起。
章节在线阅读
相关小说
网友评论
为您推荐
最新评论